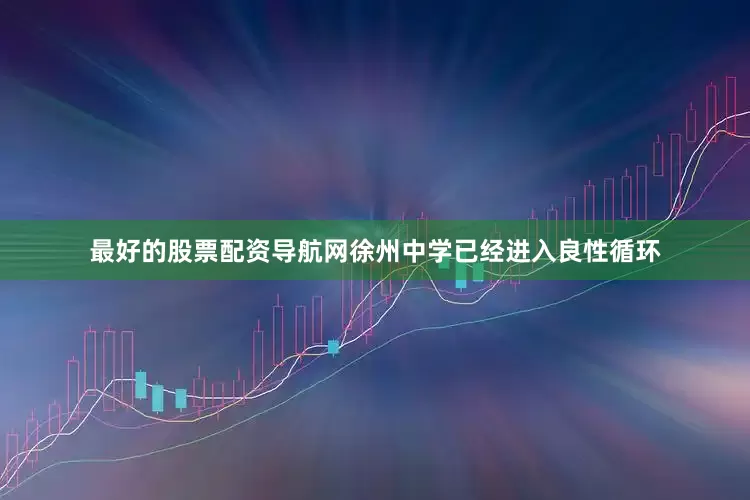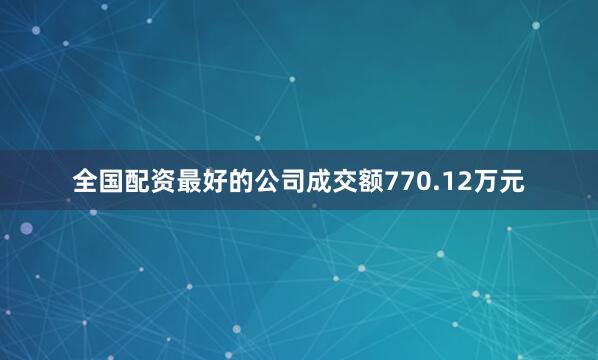暮色笼罩,老人的眼眸深邃,仿佛能穿透重重迷雾,凝望着眼前变幻莫测的棋局。那双眼,曾伴随他在将星云集的西山指挥中心,与开国元勋们一同为国家命运绸缪规划。也曾在寻常灯火下,对着年幼的孙辈,娓娓讲述戎马一生的点滴,将战场的硝火以另一种方式传递。他,便是粟裕。

时间来到1979年,中国刚刚从那场持续十年的动荡中喘过气来,正努力恢复生机,和平发展的曙光依稀可见。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南疆方向战火骤燃,一场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如同拉满的弓箭,即将离弦。全世界为之侧目,不曾想这个看似平静的国家,会突然调动近六十万大军,给两个近邻上了一堂残酷的实战课。对越自卫反击战,就这样在惊讶声中猝然爆发。
那一年,72岁的粟裕已从军队一线岗位退下长达二十一年,在北京的最高军事决策圈里,他更多是作为重要的军事顾问存在。但即便如此,他作为久经沙场的功勋战将,他的意见依然举足轻重,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
外界曾有人猜测,或许粟裕并不赞成对越南动武,觉得那是多余之举。这种看法显然低估了他作为军事战略家的视野深度。他真正忧虑和关注的焦点,压根不在南疆打还是不打的层面,而是中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直接去硬碰硬那个庞大的军事联盟——苏联。
越南之所以敢在中南半岛耀武扬威,甚至不惜把枪口对准曾经的“老大哥”中国,其最大的底气正源于1978年11月与苏联签署的那份军事同盟条约。苏联有一个险恶的“哑铃战略”构想:一头在西边掌控阿富汗、伊朗、印度,从而掐住马六甲海峡这条海上咽喉。另一头则在东边扶持越南,试图整合整个中南半岛。
它的核心意图,就是想从南北两面包抄钳制中国,将其拖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在粟裕看来,越南虽然带来切肤之痛,但它只是苏联用来引诱中国深陷泥潭的一枚棋子,真正的、悬在中国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是那个盘踞北方的巨大邻居——苏联。
对于这个北方巨邻,粟裕的了解远非泛泛。自1954年担任总参谋长起,他就一直致力于国防建设,期间多次与苏军将领打交道,也曾亲自前往苏联考察学习。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为应对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他亲赴甘肃、青海、内蒙等北方五个省份的边防地区考察,总行程超过七千公里。
粟裕有个长期以来雷打不动的习惯:在制定任何重要的作战计划之前,他必然要亲自到预设的战场区域,实地勘察地形地貌。在西北边陲那次长途跋涉中,他经常乘坐吉普车,随时要求停车下来,一步步去察看那些地方。甚至连一些直接处于苏军重炮射程内的前沿阵地,他也坚持要亲自踏足,这让当时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上将都忍不住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那次深入边防的考察结果,用“并不理想”来形容已属委婉。国防战略的实施存在不少明显的“漏洞”,其中最让他忧心忡忡的是耗费巨大心血修建的“人造山”工程。这些本意是构筑防御屏障、制造人工天险的工事,有些却莫名其妙地建在了远离后方依托的边境最前沿地带,背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
这种选址一旦被敌军围困,等于自设死地。更严重的是,许多防御工事竟然完全朝向了错误的战略方向,对着根本不可能成为主要威胁的一侧。这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式的国防规划,如果真的投入实战,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此外,历经十年动乱,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亟待恢复和检验,指挥系统层层叠叠、显得有些冗杂,基层官兵的训练不足且缺乏实战经验,武器装备也显得陈旧落后。面对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五十四个师、总兵力超过六十万,还拥有数千辆坦克和飞机的绝对火力优势,粟裕心中的忧虑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早在对越作战发起前一个月,粟裕便未雨绸缪,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名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重量级报告。报告中,他大胆地将假想敌直接锁定为强大的苏联。他精准地分析了苏军惯用的“闪电战、人海战术、钢铁洪流”这三大战术招数,并借鉴了1945年苏军横扫日本关东军的经典战例,提出中国军队应当避免与苏军进行战略决战。
他主张我军要灵活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多种形式,与敌周旋,逐步消耗敌人。同时,要大力强化重要城市的设防和预设战场体系的建设,通过立足内线的持久防御,寻找并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反攻。他尤其强调,在与苏军这种对手交锋时,不仅要集中优势兵力,更关键、更迫切的是要在局部战场上,想方设法集中火力优势。
他用那段血与火写就的历史——抗美援朝战争——来佐证这一点。他说,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是过去那种以轻武器为主、靠枪法决定胜负的时代,而是发展到了以重武器为主、胜负更多取决于炮火的较量。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火力劣势,仗就难打。火力优势,仗就好打。”这篇报告,敢于正视并挑战苏联这个巨无霸,敢于质疑当时可能存在的僵化战略战术思维定势,给全军上下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其部分真知灼见甚至很快被摘录编入军事学院的教材之中。
然而,正如报告并非主张与苏军正面硬刚一样,对越南的行动,上策并非与苏联拼个你死我活,而是高明的战略制衡。粟裕与一众老帅们反复商讨,最终确立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精妙的十六字方针:“北慢南快,先南后北,速战速决,震慑全局。”这方针的核心,就在于抢夺宝贵的时间差。
他们预判,苏联要将位于欧洲方向的主力部队调往远东,并完成大规模军事动员,至少需要十五到二十天的时间窗口。中国的军事行动,就是要利用这短短的半个月到三周的时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击垮越南的主力,彻底解决掉南疆方向悬而未决的隐患。只要能在半个月内达成既定作战目标并完成战略撤退,即便苏军集结完毕、磨刀霍霍,也已错过了最佳的出兵窗口期,失去了进行干涉的战略意义。
战事如期打响,坐镇东西两线战役总指挥部的两位高级将领,都与粟裕有着深厚的渊源。东线由威名赫赫的许世友将军指挥,他是当年华东野战军时期跟随粟裕出生入死的虎将,情谊非同一般,自不必多言。西线昆明军区的副司令员张铚秀,更是粟裕将军亲手带出来、寄予厚望的“得意弟子”。

张铚秀年轻时在新四军先遣支队时期便跟随粟裕,粟裕在战场考察时常常不吝赐教,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手把手培养他的全局观念和战术思维能力。在对越反击战西线初期,原定的杨得志将军因病倒下,张铚秀临危受命接替了指挥权。他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态势,果断调整并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指挥部队在十七天内一举突破越军经营多年的防线四十多公里,给予越军号称王牌的316A师以毁灭性打击。
他的作战风格,与粟裕颇有几分神似:极为注重战前详细的侦察,总揽全局制定策略,善于组织连续作战,并将兵力集中起来专攻敌军的精锐部队。而在北京中枢指挥部坐镇的粟裕,也并非仅是顾问角色、作壁上观。当广西方向的我军55军攻克谅山北市区、按照原计划准备停止进攻时,正是粟裕等老帅们根据对苏军集结进展的研判,力主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再给越军一次更沉重的打击。
总参谋部很快根据这个重要意见,向前方下达了“争取更大胜利”的指示。东西两线我军随即继续向南推进,做出威逼越南首都河内的态势,这极大地震慑了越南,迫使其进入了全国总动员的紧急状态。而中国军队则挟带着大胜之威,干净利落地于3月5日对外宣布撤军,整个军事行动,恰好控制在了预定的半个月左右。
粟裕将军这份对战争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他近乎执拗般的军人本色,不仅体现在国家战略层面的运筹帷幄之中,也深深融入了他对自家后代的言传身教里。粟裕与他的长子粟戎生之间的关系,被粟戎生自己打趣地称为“军事父子”,父子俩只要开口说话,话题内容几乎三句话不离军事。
从粟戎生还在咿呀学语、两岁时回到父母身边开始,粟裕就对他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吃饭不能挑食,夜间行军不能哭闹,从小就培养他军人吃苦耐劳的作风。到五六岁时,粟裕送给粟戎生一个极特别的礼物——一支战争中缴获的小手枪,他手把手教儿子射击,希望从小培养他对武器装备和军事的热爱。等到粟戎生上中学的时候,粟裕若有空闲,便会带着兄弟俩去部队靶场打靶。他自己的枪法出奇精准,常常用一根树枝顶着半个乒乓球作靶子,每次都能做到一枪击碎,令两个儿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粟戎生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当时颇具声望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工程系。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响,粟戎生一度热血沸腾,强烈渴望像前辈一样“投笔从戎”,直接到野战部队去参加战斗,但被学院领导劝阻了下来。粟裕得知儿子的想法后,虽然赞赏他敢于面对战事的勇气和态度,却也站在更长远、更深远的视角,语重心长地指出:“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你应该下决心掌握一门乃至几门真正的本领!”
粟戎生将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里,更加刻苦地学习钻研技术。毕业后,他主动要求从基层战士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随着粟戎生在部队中逐级晋升,粟裕对他的军事教导也随之“升级”。儿子担任连长时,他就教导如何去带兵、如何去爱兵、团结兵。等到粟戎生担任团、师一级的指挥员时,他们的谈话就深入到了地形图研究、战场态势分析和更宏观的战略战术层面。
粟裕一生酷爱地图,他的卧室四壁常常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甚至外出抵达一个新地方,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便是找到并挂起当地的军事地图。他要求粟戎生多看、多记地图,会随机考问某个县城的地理位置、交通要道。他尤其强调,地图在指挥员脑中应该是一个立体的概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的平面,更必须结合实地的亲自勘察去印证和补充。在父亲的影响下,粟戎生也养成了白天出行时,习惯性观察沿途地形地貌的职业习惯。

有一次,粟裕问粟戎生,如果他带领部队驻扎在某个特定地域,当遭遇敌军来犯时,应该首先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粟戎生按照惯常的思维,从敌情、我情、地形这三个方面作答。粟裕听完后,点了点头,却又补充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没有想到,那就是民情。在战场上,要是丢掉了这一条,仗是打不好的!”他告诫儿子,要深入研究现代条件下的如何进行人民战争。他还曾对着一张描绘五六个战士围攻一辆坦克的宣传画生气,认为这种宣传脱离战场实际,单纯靠人去硬抗集群坦克是“还要吃大亏的”,他再次强调,不仅要有好的武器装备,更要精通战术技术。
到了晚年,粟裕开始着手撰写战争回忆录,他总是先让粟戎生看初稿,征询他的意见。这些饱含了几十年戎马生涯回顾与深刻思考的经验总结,无疑让粟戎生受益匪浅,成为他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3年5月,粟戎生因工作需要,前往医院向病重中的父亲辞行。当时的粟裕将军说话已经非常吃力,但他依然断断续续、字字艰难地嘱咐儿子:“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这几个级别的锻炼,对军队的干部,太重要了……”这成为了父子俩之间,最后一次关于军事的对话。
1984年2月5日,粟裕将军在北京逝世。在火化之后,人们在他的骨灰中意外地发现了三块早已嵌入体内、乌黑发亮的弹片——那是五十四年前在战场上嵌入他头颅的战争印记,也或许正是伴随他多年、反复发作的头痛病根源。清明时节,粟戎生陪同母亲楚青,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了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沂蒙山等革命老区,让老帅与那些牺牲的战友们长眠一处,仿佛又回到了那战火硝烟弥漫的岁月,一同守护着这片土地。
那双似乎能穿透历史风云的目光,既宏观地凝视着波谲云诡的国际棋盘,为共和国的战略大棋局谋篇布局。也微观地关注着军队基层建设,关注着军事人才的细致培养,心心念念的是部队的战斗力和指挥员的成长。从国家战略的深邃思考,到父子灯下寻常的谆谆教诲,无不映射出一位久经战火的军事家,对战争艺术最深刻的理解,以及他对国家和民族未来沉甸甸的责任感。这目光,为新中国赢得了数十年的宝贵和平发展时光,也深深地镌刻在后来一代代军人的成长轨迹之中,仿佛从未真正远去,仍在默默地指引着方向。
东南配资-专业的股票配资官网-加杠杆最安全的证券公司-个人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